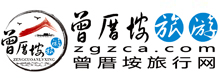眨眼十年,物是人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只是再也回不去了,那个单纯到傻的拉漂时代,来日纵是千千阙歌。我爱那时的拉萨,到死都会爱。满城风雨了都爱。
我写书,写文章。
我半路出家,我是个野生作家。
我写过很多故事,都是写别人的。
今天我讲半个自己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昔年的拉萨,那时我是个24岁的莽撞青年。
那时候我热爱远方、异乡、痛苦和沧桑、醉酒,以及漂亮的女人。
和所有年轻的人一样,我疯癫、荒唐、桀骜、交友不慎、不停地犯错。
这真是极好的。
因为没有什么比年轻时认认真真地去犯错更酷的了。
因为没有什么比年轻时一群人陪着你一起认认真真地去犯错更酷更美好的了。
可惜,光阴逝如东流水,没人能永远24岁。
当时当下,我最大的遗憾,是犯错的契机越来越少了。
不会犯错的人是停止了生长的人,恐怖恐怖,这他妈不是我想要的。
万幸万幸,好在有文章这个盆儿,可以偶尔泼泼人生这盆狗血驱驱邪。
所有犯过的错、留下的遗憾都在盆儿里了。
愿那些温暖过我的也能温暖着你,超度过我的,亦能超度正在年轻的你。
阿弥陀佛么么哒。
(一)
先从一个遗憾说起。
2007年,火车开进拉萨,阿达关了骑行者酒吧,回了广东。
2008年,拉萨3·14暴乱。
东措砸得稀巴烂,曾经的骑行者满目疮痍。
半条北京东路都稀巴烂了。
曾经的浮游吧也稀巴烂了。
和大部分的拉漂一样,08年之后我基本告别了藏地。
浮游吧没了后,彬子一度单车浪荡天涯,最远骑到了阿富汗。后来他重回拉萨,发誓要重开浮游,亚宾馆旁的旧址上重建是不可能了,他向东措的老赵赊了半间小房,在东措院子里重新支起了新浮游吧的牌子。
他给我打电话说:新浮游吧还是有你的一半。
我笑,我不要……新的浮游吧怎么可能还是最初的浮游吧,我不要!抽刀断水水更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于是彬子把东措浮游吧改名为藏藏吧,我30岁的生日那天飞去的拉萨,他偷偷买了酸奶蛋糕,逼着我坐在藏藏吧的卡座里切了蛋糕吹了蜡烛。
我捧着蛋糕,哭得和王八蛋似的。
我说彬子彬子,兄弟们呢,怎么都没了。
他说操!这不还有我吗。
我说操!只有你一个也不够啊。
第二年我再去拉萨时,连他也没了,他滚回北京生孩子去了。
那次同行的还有万晓利一家人,我和万总蹲在街头抽烟。彼时,拉萨的阳光灿烂和煦,一旁的流浪歌手在唱小小鸟……有人拿手机在拍。
半个下午万总和我怎么也摸不到打火机一直在蹭火。
我捕捉到一种很奇特的难受……难以言传。睡觉到半夜时忽然明白该怎么去描述了,但该说给谁听?我去当个瓶子吧,让我当个瓶子去吧,雨过天青云开处,者般颜色做将来 。
是年冬末,我去广东看阿达,羊城冬雨,他下血本请我吃海鲜大餐,他和我聊股票聊对冲基金,半个字不聊拉萨。
我想和他喝顿大酒,像当年那样边喝边唱老歌,他打死不肯。
我要翻脸,他先翻了,攥碎了一只蟹壳,他说:今天只喝酒,不要难受。
我不想让他难受。
我再没见过阿达。
阿达阿达,当年你赠我的那200个G音乐,如今唱响在南中国的无数古城,丽江、凤凰、阳朔……很多人靠着那些音乐开了淘碟店,养家糊口安身立命。
咱俩都有罪,各打五十大板。
阿达,我不联系你你就不联系我吗,你个扑街仔,
YOYO呢
YOYO已经变成了一个很遥远的名字。
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多年后,是在北京的蒙古人餐厅,大局,很杂的一个局,她和别人换了位置悄悄坐在我右手边。
我弹烟灰,她把烟灰缸悄悄推过来。
我抬头:YOYO……
她眼睛弯弯的,说:嗯……
大昭寺广场煨桑的烟气升腾在身畔,没有什么久别重逢,多年的别离仿佛只隔了一天一夜。
温暖的YOYO,善意的YOYO,窝心的YOYO。
我醉意有七分,脑袋沉沉的没有地方放,放在她的纤弱的肩头,扑鼻的香水味道,不是桂花……有人过来敬酒,她扶正我,替我挡酒,杯子举得高高的酒来杯干。
一片喧嚣里,我看见当年送她的铁戒指她还戴着,只不过被另一枚铂金戒指套在了里面,那枚戒指闪闪亮,是钻石吧,是啊,是钻石。
我醉得快出溜到椅子底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她陪着我,就这么坐着吧,挺好的,这么静静地坐着,一直到筵席结束,再没说一句话。
曲终人散时,门外下起了细雨,我陪她一起踩着积水打车。
我摇来晃去地走,横冲直撞地走,她扶着我,她帮我捡起掉在积水中的手套,然后轻轻关上车门。
我们互道再见了吗?我醉了,我忘了。
车停在原地,没有启动,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良久,车开走了,尾灯闪烁,红色的光芒晃动,越来越远。
好像一根长长的绳子绷紧了,拉着我拽着我朝着那辆车开走的方向小跑起来。
怎么可能追得上,越来越远了。
我打了一辆车去追,追上一辆不是,再追上一辆还不是。
午夜的三环路凛冽,胎噪声清晰刺耳,我摇下车窗喊:YOYO!我找到答案了!
我喊: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找到答案了!
她望着我,没有摇下车窗,只是望着我。
飞驰的高楼大厦,石头一样沉的暮色,我看不清她的脸。
我从手机里找出那首《千千阙歌》,手伸出车窗外使劲举高。
疾风如刀,把音符割得七零八落。
我喊:YOYO,你听哦!
“……
如流傻泪,祈望可体恤兼见谅
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
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飘于远方我路上
来日纵是千千晚星 ,亮过今晚月亮
都比不起这宵美丽 ,都洗不清今晚我所想
因不知哪天再共你唱
……”
(二)
彬子、阿达、YOYO……十年前,他们都还在我身旁。
十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东措青年旅馆的院子里唱歌。
手鼓轻敲,骑坐在骑行者酒吧的门口栏杆上。
拉萨的夜空是墨蓝色的,染得敲着鼓的手也变成蓝色。阿达关了酒吧的灯,拎出一把吉他搬来一箱拉萨啤酒。两个人唱一首干一瓶,不打酒官司,酒下得畅快。
夜风轻送,举头乱云飞渡,人渐至微酣。
阿达是广东佬,在东措青年旅馆开了个骑行主题的“骑行者酒吧”。他是当时藏区知名的骑行侠,九十年代骑自行车走完全国后,2000年左右骑来拉萨隐在这一偶。
他的酒吧是当时骑行客来拉萨必聚的据点,我在他的酒吧结识过不止一个骑着老式28锰钢漫游中国的老人,车上插满旗子,驼包上挂着横幅。也认识过不止一个骑车横穿欧亚大陆的年轻过客:有满脸黄胡子的间隔年大学生,有扎马尾辫的日本青年,有曲线完美到死的斯堪的纳维亚姑娘,还有一拨接一拨的理工科大学生。
当年骑行客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怪侠“鸡毛”也酷爱厮混于斯,一身盔甲肩头两根翎毛,背后别着一把尺长的战术军刀。
我俩初次见面时因为气场相左差点打起来,他斜着眼看我,我横着眼瞪他,我们握了15秒的手,他差点捏断我的指骨。接着就是拼酒,他不知道我是山东人,被灌翻在桌子底下。
鸡毛后来在拉萨为了义气拔刀捅死了人,然后亡命天涯不知所终,被通缉到今天也没归案。
阿达当时在拉萨自己做了个非法的音乐电台,经常有事没事操着一口虾饺普通话过DJ瘾。他收集了四百个G的音乐,我百般央求才拷贝出二百个G。
阿达收集的音乐全是宝贝:除了国内外知名乐队乐手的完整专辑,竖琴音乐、印度西塔琴、坎布拉手鼓合集、巴伐利亚约德尔山歌、彼得罗斯山地风笛、老挝禅乐……世界各地哪儿的音乐都有,甚至还有一小段罕见的十二木卡姆原始录音。
几年后我把那二百个G带回丽江,借给几个熟人拷贝了几份,其中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靠那部分音乐为基础,开了盗版淘碟店,并连锁了整个古城败坏了丽江十年。
当年我问阿达是怎么搞到这些好东西的,他笑而不语。只教我一个小方便法门,他让我遇见他国的旅行者来酒吧消费,就免费请他们喝酒,喝大了以后让人家用CD机或MP3里的音乐来换。他说:哪个出远门的旅行者不带点音乐啊!我深以为然,但收获颇微,因为等我开始学着做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民都已经开始流行用苹果IPOD了。
那天晚上我和阿达边喝酒边唱歌,我用白话唱《千千阙歌》,他捂着耳朵听。然后龇牙咧嘴的很痛苦地骂人,他说:“你个扑街仔,都毋知你唱咩……”
不理他,反复唱着自己最中意的那句: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
阿达那时已年过三十,是个矫情的文艺大叔,他用DJ的口吻说:“这就是老歌的魅力,一句老歌,刹那就会掀起铺天盖地的往事,像猛地掀翻的五斗橱,曾经藏匿的、貌似已经遗忘的,忽然一下子就全铺陈在你面前。人一怀旧就容易老,所以,还是不要经常听为妙。”
我笑话他说:“你他妈说得好像历尽劫波,储存了不知多少前尘往事似的。”
阿达笑笑不说话,欲言又止地看看我,抬手又是一口酒。
那时候我还太年轻,刚结束了一段感情,自以为饱经沧桑,实际却还是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孩子呀,轻易地就能给自己营造出一坨一坨的自我感动,动不动就自己撕开小伤疤往里面滴盐水。
反正,我记得我动不动就老爱唱这首歌。
教会我这首《千千阙歌》的长发姑娘早已不知流落在何方。
她总是把牛奶说成“流莱”,把六说成“陆”,她把白话和重庆话夹杂在一起絮絮叨叨的声音,早已融入了我的心跳声中。
她在广州状元坊的窄巷子里对着我哼唱:“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当时有风,她粟色的发丝不时逸到我的眼畔。
我向她求婚,她不说话,垂下眼帘,把耳朵附在我胸口听我的心跳。
她牵着我的手去吃双皮奶,挤在人群中扭头问我: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
她消失了以后的多年间,我去了漠北,去了南沙,去了可可西里,去了我所能触及的每一个天涯。
遗憾的是,这句话直到今天也不知该如何去回答。
可是在我24岁时,我自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一度认为那个答案,叫做西藏。